最新:《通往魔法之地》:当生命走到中途,我们怎么办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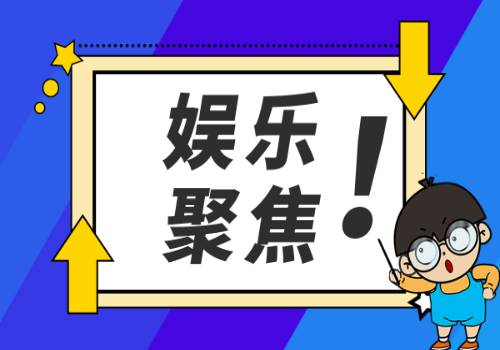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三位发小从世界的不同地方一齐奔赴偏僻的苏格兰小镇重聚。既然是闺蜜,她们自然会分享这些年生活里的不如意,未曾想,却在不经意间揭开了各自深埋的隐痛,甚至暴露出她们曾刻意压制的、令人难堪的、为他人制造痛苦的秘密。传言中的魔法,似乎在验证量子纠缠,生态村里的人接通了“宇宙天线”,如同穿行与己相关的不同时空,由爱生发的各种事件缠绕每个人。外人目睹事件的过程与结果,只有自己才知晓事件的动因。人生已过半程,雷鸣、冰子、李小妹与真实自我渐行渐远,小镇相遇不是一场集体忏悔,而是一次追溯与澄清。那么,友谊在所有真相都被曝光后,是彻底决裂还是勉力维持?
雷鸣脸上总挂着笑示人,她永远保持高扬情绪。经历了结婚、离异、出国、再婚,中年的她,沉浸于神力,“竭尽全力用她的世界观改造你的世界观。”冰子是学霸人设,赴美多年,曾就读耶鲁医学院,妥妥的成功人士样板,但一度与“我”断联。“我”叫李小妹,程式化地读书、就业、成家,从乏味的成人学校离职后,专心做一名网络作家,此时正经历中年危机。李小妹的心思十分精准地透露出三人关系——“我经常想到她,却又希望自己忘记她。”
成长,或许说心理的真正成熟,是这趟“魔法之旅”的核心收益。我们读过很多小说,强调主人公“为他人”所思所想,实则伤害自己,唐颖却在这部作品里讲述“为自己”给个人造成的持久困扰。她将三人的成长,切分为两个阶段。在第一阶段里,我们惊讶地发现青年时代的雷鸣、冰子、李小妹,竟然对家庭都缺乏耐心,她们对婚姻不抱什么热切期待,因此很少展开经营婚姻的行动。“我们这代女人都是铁娘子,哪怕表达情意也是带着火药,我们是在上一辈的争吵或者争辩,或者斗争,whatever,反正是在火药味中学会讲话。”“唯我”“排他”被刻入基因,再加上先前的情感挫折早已戳破情爱幻梦,她们其实有着相似的理性,清楚个体所需,颇为一致地对他人始终有要求。
三位闺蜜拥有不同版本的私人生活。唐颖设计了双重叙事视角,通过他人陈述和自我陈述的转换,冲击着已然的真假,从不断叠加的家事、情事中剥离出真相。小说借雷鸣之口、李小妹之眼触及量子力学,作者虽没有对此铺开详细论证,但事实上,将“薛定谔的猫”化入了创作理念。只有揭开盖子才能得知猫的生死,可一旦将其揭开,触动电子开关,猫则毫无生机。她们先前都只向外界输出可对人言的部分事实,正因为确有遮掩,故而总有一些难解之处。当三人说出真相后,所有卡点全然畅通的同时,友情濒临破裂。
人物经历的第一个版本,唐颖未安排当事人现身说法,而是借由旁人转述。雷鸣叙述冰子的事。在接李小妹的途中,她细述冰子的两段婚姻和两个孩子,更爆出其罹患忧郁症且曾经自杀。李小妹披露雷鸣的过往,穿透其父母的联名画作,拨开他们的家庭悲剧。人物经历的第二个版本,即其真正人生,皆是自己讲述的。雷鸣坦陈前夫是性欲狂,李小妹透露了堕胎史,冰子吐露出她曾经如何从李小妹手上抢夺了萧东,得到并不光彩的一段婚姻。相比李小妹和冰子,雷鸣更为悲情,也最有特色。她才是实施自杀的那个人,因其习惯报喜不报忧,故而受困于心理层面的悲喜交夹。当童年面对家变的时候,她就开始向外界表演。“那天下午玩滑梯——我现在不记得那是公园的滑梯还是幼儿园的滑梯——轮到雷鸣时,她站在滑梯上面,准备往下滑时,她原本是笑着,却在瞬间瘪着嘴要哭了,但她马上从滑梯上滑下来,从地上站起来时,她在笑,一看就看出,是装出来的笑。”“我”终于明白她站起来的那刻,为什么还会笑?她因惧怕而不知所措,于是先用笑抵抗失父的痛,说服自己躲开现实。雷鸣独自竭力抵抗孤独,接踵而至的不幸纷纷砸落,她就寻找各种机会令自己哈哈大笑,但一直无法摆脱心灵的空虚和悲伤,所以她选择了相信灵异。
成长的第二阶段是由小镇开启。初相见,三人互探对方底线,作者揭穿闺蜜的真实心理,既慨叹对方过得不好,又会有一种幸灾乐祸念头的萌生。例如,当“我”获悉被萧东和冰子同时欺骗后,“我”耿耿于怀,却也并未无法释怀,原因是“我知道冰子不好受了”,这反而让“我”好受很多。李小妹格外惧怕蛇,“它用身体缠绕猎物,边缠边收紧,直到猎物窒息而死,然后把猎物挤成长条吞下。”蛇是一处隐喻,它是人的欲念,扶植嫉妒、仇恨、情欲,阻止三人重建友情。这部小说的特质是唐颖没有用刻意的宽宏大量来消弭隔阂,呈现突兀的圆满,它冷静地告诉读者,什么才是生命中相对更重要的、更应在意的内容。“生命走到中途,常有荒芜之感,时间流向虚无,朋友只会越来越少,越新的朋友越容易离开,连接的纽带脆弱,因为精神上无法接近。而我越来越念旧,需要老朋友,需要老朋友带来的存在感,她们身上有你的成长印痕,因为你看不到你自己。”人需要放心托付的朋友,也需要棋逢对手的朋友。“心灵交流会”最终促成“背叛”的曝光,真相总是伤人又伤己。交流会恰如一个磁场,彼时天空出现极光,其本质为一种能量的消耗,此刻指向个人恩怨的最终散佚。李小妹心头燃烧的愤怒,终究是熄灭了。
小说运用“平行宇宙”概念构思文本。一是空间的平行。上海街区与苏格兰小镇维持平行,友谊是聚合两个空间的能量点。在雷鸣的生态小镇里,三人说着上海话,吃着上海菜,复盘上海的少时生活。“我希望雷鸣明白,我来到苏格兰更希望三人聚在一起聊天,这么多年,我们没有过三人聚的机会。人生走着走着,遗失了不少东西,包括朋友。如今称得上‘闺蜜’的朋友,就剩下冰子和雷鸣了。”空间皆为“出发”储能,流动着亲密与猜忌。雷鸣和冰子“正在摆脱物质社会的诱惑,在朝更精神化的生活靠拢。然而,她们同时也带来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气息,那是我们的出生成长年代,缺衣少食的年代。”小镇创设生活模式的复归,促发平和心境的归位。一是情感关系的平行。李小妹、冰子、萧东曾发生一段对三人皆具摧毁性的三角恋,十年后,李小妹、冰子、邓布利多三人之间,又再次衍生暧昧的情感纠葛。两组空间的链接点,是李小妹像邓布利多已去世的前女友。邓布利多严格禁欲,掩藏内心的一段伤情,他无法承认因个人执迷飙车而导致女友的死亡。机场偶遇的李小妹,恰与其女友有复刻的容貌和习惯,激活他对人生的希望,对感情的期待。对于中年人而言,婚姻是沉闷的,可也是结实恒定的。也许,“我”可以与邓布多利发生一场“我”期待已久的刻骨铭心的恋爱,但“我”及时撤出了。“我从来都是社会和人际规则的遵守者,我对自己的违规行为,有一种更深沉的恐慌,就像意识到自己正在失智却无法控制。”理智敲打“我”,将“我”从幻梦中拖拽出来,“我”自愿接受责任感和道德感的约束。
小说多次出现三人围坐一起织毛线的场景,这是十分巧妙的“破冰”。它是一种充满年代感的特殊沟通方式,能迅速引领她们回到熟悉的青少年(时间)、回到上海(空间),充分调动共同的记忆与共同的体验。同时,每个人偏爱的毛线颜色不同,掌握的织法不同,暗示各自对人生的不同规划。“当年丰沛的感情,无论快乐还是痛苦,到了今天到干涸了。我更像个观众,面对一出陈旧的肥皂剧,因尾声的仓促而意犹未尽。”她们其实都置身“干涸”的现状,唐颖用织毛线细节,制造过去和现在的互搏,三人从翻转的比较中,了解个人且认清对方,最终以沉默地织着毛线,与命运达成和解。
爱丁堡机场长途巴士站的铁铸长凳,像冰一样硬冷,初来乍到,李小妹极为坐立不定,而一位英国老妇却泰然自若。充盈于小镇的魔法是化解人的私心私欲,短暂度假令所有人懂得不再以自设标准限定他人,无需伪装自己去迎合世界。小镇确实是一块福地,所谓养生、冥想、修行流于形式主义,勇敢地敞开心灵,感受拂面而来的宽容与自由,才是魔法的奥义。
对于中年人来说,无论你已经走了多远,终究还会回来。与其心怀怨念地负重前行,不如停下,毕竟放下即放过。
- 最新:《通往魔法之地》:当生命走到中途,我们怎么办? 2022-12-06 16:17:46
- 【全球快播报】白艳茹:小镇故事 2022-12-06 16:05:22
- 新动态:新高考赋分换算公式是什么-新高考为什么要赋分 2022-12-06 16:06:18
- 新高考赋分换算公式是什么-新高考为什么要赋分 2022-12-06 16:18:11
- 实时焦点:全国最热门的单招专业-单招专业分类介绍 2022-12-06 16:07:59
- 全国最热门的单招专业-单招专业分类介绍 2022-12-06 16:17:40
- 当前快讯:新高考改革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-新高考改革变化 2022-12-06 15:56:27
- 文化丨耳闻忠言诤言之谏,自当从善如流 2022-12-06 15:56:03
- 平面设计师的工资待遇怎么样-平面设计的就业前景怎么样 2022-12-06 16:08:09
- 今日热闻!单招学历和统招一样吗-单招和统招的区别 2022-12-06 15:57:53
- 【世界新要闻】单招学历和统招一样吗-单招和统招的区别 2022-12-06 15:59:31
- 今头条!公共 | “湾区文采会”:搭建新场景 引领新趋势 2022-12-06 16:13:06
- 每日热讯!广州文化旅游场所陆续恢复开放 2022-12-06 16:08:34
- 每日观点:天津2023年初级会计职称准考证打印时间及入口 2022-12-06 16:06:49
- 大同军考培训:军考培训机构前十名 2022-12-06 16:17:54
- 学生辱骂老师,老师飞踢学生,师生之间何以粗蛮至此? 2022-12-06 16:11:45
- 环球观热点:怀化市启航卫生学校2023年有哪些专业 2022-12-06 15:58:47
- 全球快讯:研究生每月工资多少钱-各大学研究生工资分别多少 2022-12-06 16:03:00
- 长春理工大学函授本科去哪里报名 2022-12-06 16:06:44
- 天天信息:山南市着力筑牢文物安全防线 2022-12-06 16:01:48
- 环球快播:2023年四川初级会计职称准考证打印时间及入口 2022-12-06 16:12:25
- 快资讯丨山东省图书馆12月7日恢复开放 2022-12-06 16:05:54
- 世界观点:看得懂的学术通识书搭建亲近经典的桥梁 2022-12-06 16:11:09
- 焦点快报!长春理工大学函授本科去哪里报名 2022-12-06 16:02:11
- 每日观察!呈现西汉珍贵文物 2022-12-06 16:11:58
- 2023年湖北初级会计职称考试时间及科目:5月13日至17日 2022-12-06 16:17:32
- 12月5日新疆兵团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 2022-12-06 15:54:50
- 山东省图书馆12月7日恢复开放 2022-12-06 15:55:48
- 拿出真招实招上好美育必修课 2022-12-06 15:57:23
- 当前快讯:南京小伙的逆袭故事火了,梦想应该被呵护 2022-12-06 16:10:29
- 消防安全 伴我成长 2022-12-06 16:08:55
- 共建共享 推进三地文旅深度融合 2022-12-06 15:56:45
- 环球热点!南京小伙的逆袭故事火了,梦想应该被呵护 2022-12-06 16:04:19
- 2023广西初级会计职称准考证打印时间及入口 2022-12-06 16:13:00
- 世界播报:大学生上3年半网课完成结婚生子,引网友羡慕 2022-12-06 16:16:47
- 今日视点:12月5日新疆兵团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 2022-12-06 15:54:42
- 天天观点:积极主动作为 推动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2022-12-06 16:03:50
- 天天快消息!一建成绩合格标准22 2022-12-06 16:15:24
- 快看:西藏已建成5G基站8099个 2022-12-06 16:06:59
- 让文化自信种子早早播撒在孩子心中 2022-12-06 16:14:53
- 全球热议:2022一建成绩考后多久出来 2022-12-06 15:57:35
- 免联考MBA含金量和优势怎么样? 2022-12-06 16:06:25
- 全球观热点:在职博士怎么报名? 2022-12-06 16:10:02
- 2022下半年重庆小学教师资格证查分时间及系统 2022-12-06 16:01:56
- 【全球热闻】2022下半年陕西教师资格证笔试查分系统 2022-12-06 16:10:01
- 全球新动态:新会计准则下建筑企业怎么收入确认? 2022-12-06 16:03:51
-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怎么计算? 2022-12-06 16:12:43
- 高会评审申报前换单位 对评审有影响吗? 2022-12-06 15:54:00
- 天天滚动:企业拆迁补偿五年账务处理 2022-12-06 16:08:30
- 当前消息!中级会计师备考赶早不赶晚! 2022-12-06 16:17:42
